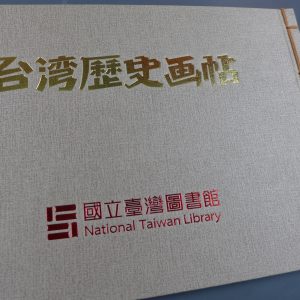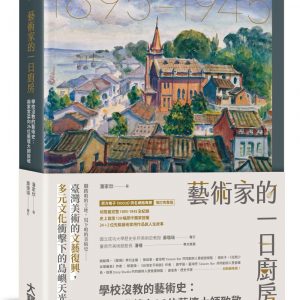撰文|陳韋聿
顏水龍 臺展第1、3、7~10回,府展第1回
特選 臺展第3、7回
審查員 臺展第8回

輪船離開東臺灣海岸之後,越過大片的汪洋,覆滿了綠色植被的紅頭嶼,便會從海平線的彼端漸漸浮現。那是日治後期,仍舊原始的小島上沒有港口,龐大的渡輪只能在外海拋下鐵錨,等待腳船的接駁。
而這一刻,年輕的顏水龍正在船舷邊緣攀著繩梯,準備頂著風浪,冒險跳上一艘拼板舟。成為畫家之前,他大概從未想像過有這麼一天,自己竟會飛躍在太平洋上,只為了前往僻處海外的一座島嶼。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:這座島上的人群與故事,竟然會變成他往後的藝術生涯當中,一個至為重要的命題。
***
1935年,居住在日本的顏水龍,趁著返臺參與「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」繪畫委託工作的難得機會,決定安排一段空檔,造訪紅頭嶼。
──該說是一個挺古怪的願望吧。據說在此之前,未曾有任何一個出身臺灣的畫家踏上紅頭嶼。從來是極少數人願意主動前往的陌生異域,去那裡做什麼呢?
有趣的是,顏水龍也確實像是一個要前往部落蹲點研究的人類學家。為了這趟旅行,他事先走訪了臺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學教室,研讀關於紅頭嶼及島上住民的調查資料。之後,顏水龍甚至還將他的見聞與觀察,寫成了一篇類似田野筆記的報導文章,刊載在日本的新聞雜誌上。

很難知道這趟遠行的念頭究竟是怎麼開始的。不過,我們的確能夠從顏水龍的早期生涯當中,窺見他對於臺灣原民文化的熱烈興趣。在紅頭嶼,他仔細地審視島上住民的日常器用,包括餐具、水甕、鍋爐,乃至於表現生活情趣的土偶玩具等等。在顏水龍的眼裡,所有這些就地取材的自由工藝,除了具有實用價值,同時也蘊藏著豐富的地方特性與創造力。
除了關注原住民的傳統文化,身為美術創作者,顏水龍同樣沒有擱置畫筆。他將自己的宿舍布置成了簡單的作品展示間,並以前來參觀的島民為對象,作成一張又一張的人像素描。與此同時,顏水龍也走訪部落的裡裡外外,四處觀察島上的日常生活圖景。其中一幕,特別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那是紅頭嶼的凌晨或午後時分,島上的女人們總會帶著陶壺到海邊汲水,再頂著這些沉重的容器,成群結隊地踏著浪花,返回部落。「宛如印象派畫家的作品」──顏水龍如是描述那樣一種美麗光景。而在當年的臺灣美術展覽會裡,他也將同樣的風景印象,展示在本島人民的眼前。

***
時移事易,二十世紀中葉,整個東亞世界經歷了二次大戰的洗禮。新舊更迭,同時意味著傳統文化的迅速消逝。當顏水龍再度踏上那座已被更名為「蘭嶼」的小島,已是1970年代的事情。這次,他所乘坐的輪船,終於能安穩地駛進現代化的港口靠泊。
然而在岸上,他卻驀然發現:眼前的一切風景也幾乎被現代化的巨浪所吞沒──觀光客從窄小的港口蜂湧而入,精巧的傳統工藝被粗製濫造的廉價商品所取代。種種景象,都與記憶裡的紅頭嶼截然不同。
那時的顏水龍已年近七旬,卻未曾失去對於這座島嶼的美麗想望。闊別三十餘載,這位畫家依舊熱切地描繪島上住民的深邃面孔,以及拼板舟的裝飾與造型。他總是喜歡太陽,在他的心目中,太陽的顏色,就是代表臺灣的顏色。而在蘭嶼,顏水龍也將陽光塗成了溫煦和暖的油彩,照亮了畫布上的土地與海洋。
結束了1972年的旅行以後,顏水龍仍持續不斷地返回蘭嶼,試著用畫筆紀錄眼前還未消逝的一切風景。生涯晚期,他完成了許多以蘭嶼為題的傑出作品。所有這些畫作裡的原住民、拼板舟、陽光與海,也自此成為臺灣美術史上一種深具代表性的圖像。


從日治到戰後,跨越兩個時代的蘭嶼旅行,在顏水龍豐富多彩的藝術生命裡,是一個頗為特殊的篇章。生涯中、後期,他積極投入臺灣本土工藝的研究與推廣,試圖將美學元素帶入日常器用,藉以充實社會大眾的生活內涵,同時也希望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。而在顏水龍的蘭嶼畫作當中,人們會發現:他是如此熱切地描繪一座人間樂土般的島嶼。在那裡,世變引致的失落與斷裂都已不復存在,關於未來,畫裡或許就有我們想要的答案。
透過藝術,顏水龍不斷提醒我們珍視過去,從在地文化當中發現屬於自身的美學。那樣的土地情感與現實關懷,或許也是顏水龍的種種作品,最想傳達給我們的事情。

參考資料:
關於顏水龍在1935年的蘭嶼之旅,種種細節,參見顏水龍等,〈畫家眼中的蘭嶼〉,《雄獅美術》,75(臺北,1977),頁56-71;顏水龍文、圖、劉子倩譯,〈原始境紅頭嶼の風物〉,《週刊朝日》,28:11(東京,1935年9月8日),頁24-25,收錄於雷逸婷編輯,《走進公眾‧美化臺灣》(臺北市:臺北市立美術館,2012),頁374-381。〈附錄:三次採訪顏水龍錄音檔1988-1989〉,收錄於雷逸婷編輯,《走進公眾‧美化臺灣》,408。
關於顏水龍在生涯早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所流露的興趣,參見黃莉珺,〈顏水龍原住民題材畫作研究〉(臺南市: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,2003),頁22-24。
#名單之後017